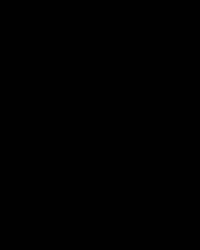云绾宁墨晔小说>皇明 > 第253章 铁骑夜袭明军破阵(第4页)
第253章 铁骑夜袭明军破阵(第4页)
莽古尔泰眼中露出精光,对着众人说道:“诸位,我便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军令既下,整个大营顿时沸腾起来。
号角声撕破雨夜的沉寂,火把如游龙般在营帐间穿梭。
两蓝旗的精锐铁骑如潮水般涌出营门,沉重的马蹄将泥泞踏得飞溅。
黑暗中,箭囊与刀鞘碰撞的脆响,战马马蹄的清脆声,还有士兵们压抑的喘息,都在预示着。
这场血腥的屠杀,即将拉开帷幕。
另外一边。
分水坝东侧的密林中。
贺世贤甩了甩湿漉漉的须发,酒气混合着血腥味在胸腔翻涌。
他卸下厚重的铁甲,只着轻便皮甲,腰间长刀随着战马的颠簸不断拍打大腿。
泥泞中行军留下的痕迹,像一条蜿蜒的伤疤,直指黑暗中的东坝。
雨水虽已停歇,但林间仍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混合着将士们身上铁甲的锈气。
“贺帅,前方探马回报!”
亲兵压低声音道。
只见一名斥候从灌木丛中钻出,单膝跪地:“禀大帅,东坝驻有建奴一个整编牛录,约三百精锐。坝上遍设哨塔,外围挖了陷马坑,还布了铁蒺藜。若要强攻,恐怕会有巨大的伤亡。”
贺世贤闻言,醉眼猛地一睁,手中酒囊啪地砸在地上。
残余的烈酒渗入泥土,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巨大伤亡?”
他一把揪住斥候的衣领,浓烈的酒气喷在对方脸上。
“半个时辰内,老子就是带着弟兄们全交代在这儿,也得把东坝给炸了!”
虽已连饮三碗烈酒,贺世贤布满血丝的双眼却愈发锐利。
他抬手抹去胡须上凝结的雨珠,铁甲下的肌肉随着急促呼吸起伏。
这位身经百战的沈阳总兵,此刻正如绷紧的弓弦,将醉意与血性尽数化作凌厉战意。
“探马听令!”
那斥候尚未起身,便被贺世贤的铁手套一把按住肩甲。
“给你们一个任务,半刻钟内,给本帅摸清东坝虚实陷马坑、铁蒺藜布防在此处?哨塔几座?火炮位可曾架设?不必精细,但若漏判一处要害,军法从事!”
那斥候闻言,咬了咬牙,点头道:“属下领命!”
情报收集工作安排好了。
贺世贤转身看向身后精锐骑兵。
千余名铁骑早已在雨中列阵。
这位沈阳总兵当即发号施令:
“传我将令!”
“骑兵分作三队,每队五十骑!第一队!取我贺字大旗,沿东侧山脊擂鼓!第二、三队持双火炬,绕西面、北面松林作疑兵!记住!要喊得比建奴的丧钟还响,逼他们分兵三处!”
亲兵立刻捧上令旗,贺世贤一把抓过,猩红的旗面在风中猎猎作响:“每队配双倍火把,大张旗号!让建奴以为我大明主力尽出,把他们的弓箭手都给我引出来!”
夜风骤急,吹得火把明灭不定。
贺世贤深吸一口气。
“再选五十死士!尔等持木板沙袋,为大军开道!见着鹿砦拒马,就给老子烧!烧出一条血路来!”
此话一出,便有五十人出列。
做死士是最危险的事情,却也是最能立功的。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