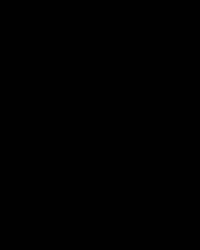云绾宁墨晔小说>皇明 > 第280章 积愤待发草原战起(第3页)
第280章 积愤待发草原战起(第3页)
努尔哈赤刚下了令,要将他们的家眷都送往赫图阿拉当人质,李延庚这逆子,终究还是逃不过去。
帐篷外的两个侍卫见他走来,立刻单膝跪地行礼:“将军。”
李永芳摆了摆手,声音低沉:“你们都退下吧,今后不用再来看管这畜生了。”
侍卫们愣了一下,对视一眼后不敢多问,再次叩首后便转身离去,脚步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
风卷起帐篷的边角,露出里面昏暗的光线。
李永芳站在帐外,能隐约听到里面传来翻动草席的声音。
那逆子还醒着。
他深吸一口气,伸手撩开了帐帘。
李永芳刚迈过门槛,就见李延庚背对着帐门,蜷坐在一堆干草草席上。
他的头发像一蓬乱糟糟的枯草,黏在汗湿的额角,裸露的胳膊上满是抓挠的血痕,显然是这些日子在帐里焦躁难安,连觉都没睡踏实。
听到脚步声,李延庚猛地回过头,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像困在笼子里的狼,亮得吓人。
待见是李永芳,他又“嗤”地冷笑一声,重重转回去,脊梁挺得笔直,仿佛那背影都在说“不屑一顾”。
“怎么?连我这个父亲都不认了?”
李永芳走到他对面坐下,帐内昏暗的光线下,能看到他鬓角新添的白发。
李延庚攥紧了拳头。
“父亲?你也配当父亲?”
他猛地转头,目光像刀子似的剜过来。
“那些建州畜生在营里抢咱们的粮、扒咱们的衣,连弟兄们的婆娘都不放过,昨天张老五的闺女被拖走时,哭得撕心裂肺,你听见了吗?”
他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咱们汉人在这儿活得不如狗!你倒好,还帮着努尔哈赤当差,帮着他欺负自己人!这样的卖命,有什么意思?”
李永芳的喉结滚动了一下,避开儿子的目光,看向帐角那堆发霉的干草:“不能忍,又如何?”
“反了啊!”
李延庚几乎是吼出来的。
“刘兴祚能反,咱们为什么不能?去投大明,总比在这儿当猪狗强!”
“反?”
李永芳苦笑一声,声音低得像蚊子哼。
“刘兴祚能反,是因为他手上没沾多少明军的血。我呢?”
他抬起头,眼里满是血丝。
“我是第一个献城投降的明将,抚顺城破那天,多少明军死在我手里?多少百姓因为我而降了建奴?现在去投大明,人家能容我?怕是刚到沈阳,就被熊廷弼砍了脑袋祭旗!”
他的声音带着颤抖,像是积压了多年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出口:“为父不是不想反,是不能反!咱们全家的命都捏在努尔哈赤手里,一步踏错,就是满门抄斩!”
“可大明皇帝的招降令写得明明白白!‘既往不咎’!只要咱们立了投名状,过去的罪过全不算数!父亲难道连这都不信?”
他眼里闪着执拗的光,仿佛那道招降令是黑夜里唯一的星火。
李永芳看着儿子这副模样,忽然想起自己刚降建州时的光景。
那时他也以为能靠着“识时务”换来安稳,如今才知,在这乱世里,所谓的承诺轻得像鸿毛。
他苦笑一声,声音里带着浸了多年苦水的沙哑:“你没在辽东官场待过,不知道那潭水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