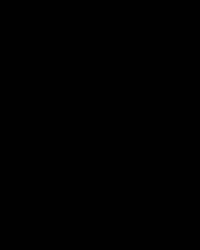云绾宁墨晔小说>啊这不是乙游嘛? > 8090(第14页)
8090(第14页)
“既然知道,就该知道那是一种类人却非人的生灵……”阿缇耶张了张嘴,没再接着故弄玄虚,而是继续说了下去:“在更早之前、早在第一次灭世的大灾难到来之前,卡洛斯的城主之位始终就是空缺的。”
“若要从现在保留的历史正文记录来看,那么应该是那位升任为帝国议长的城主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下一位了。”
非常不合乎常理的安排,对吧。
可在当时那位金血暴君的刻意操作之下,这种完全无法理解的特殊安排,偏偏也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发生了。
“一开始,人们以为这是君王对宠臣死后仍存的偏爱,最后一段要计入历史的证明,可随着继任者登基上位,准备开始为卡洛斯安排下一位新的城主的时候,他们又发现,好像不仅仅是这样的……”
阿缇耶说到这儿时特意停了停,又一次意味深长地提醒我,您确实知道妖精是什么东西,对吧?
我看向她的眼睛,也配合着再次点点头。
那就好了。她微笑着回答,妖精嘛,喜欢模拟人心,却又不通人心,祂们在上一任主人的操纵下对守护卡洛斯的任务早已厌倦,只想等着她的死亡一同带走愿望的束缚;
至于卡洛斯代表了什么,那不败的城墙又承载了万千民众何等沉重的心愿,这些对妖精来说,全部都是无所谓的。
妖精们所承诺的永恒,仅仅限于许愿的那一刻开始、许愿者的寿命到达极限的那一天为结束。
当最初的祷告者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妖精们便也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也可以从这片城墙中离开了。
是这么想的没有错。
一开始,无论是祂们,还是他们,都是这么想的,没有错。
“……可是直到现在,卡洛斯仍然存在。”
“是呀,它还在。”
阿缇耶笑着说。
“——因为最初的领袖已言,它必然要是永恒不败的城。”
即使这世界已经数次坍塌崩溃成虚无的废墟,唯独名为卡洛斯的梦依旧永恒不朽。
“大概是某一天,妖精们忽然发现,祂们其实早已被名为永恒的梦捆死在了城墙之中,再也无法离开了。”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太痛苦了,太绝望了,最不可能的发生的事情已然发生,惊恐之后便是铺天盖地的憎恨与怨毒的诅咒,被同最初心愿一起砌入墙中的妖精们开始渴求着久违的自由,祂们疯狂诅咒着最初祈愿的那个人,也同时对后续坐上城主之位的人无数次伸出手,给予他们可以无限许愿的慷慨承诺。
因为最初那人的位置早已站得太高,寻常人的愿望根本撼动不了她留下的痕迹。
不过还是那句话。
妖精嘛,喜欢模拟人心,偏又不通人性。
无数人因妖精的承诺而心动,可惜这些人许下的愿望无外乎也是那些久违的老套路:财富,权力,地位……妖精们多好用呀,只要祂们仍然留在这里,那么就等同于拥有了无穷无尽的许愿机。
于是,这一次换做妖精们开始重新愤怒了。
祂们依旧憎恨最初的人,却也更厌恨后来的人。
那些浅薄的心愿开始被主观的扭曲,改写,随心所欲地挑选结束的时间,继任者们的血几乎溢满了那冰冷的城主椅,直至成为某种不可名状的诅咒,再也没有任何一人有勇气接过卡洛斯的权柄。
这样的诅咒持续了很久呢,阿缇耶感慨着表示,久到哪怕到了现在,卡洛斯的指挥官的位置也依旧常年空缺。
人类何等傲慢,灭世的灾难都无法摧毁连卡洛斯的城墙,几个所谓的大人物,偏偏却觉得自己可以想办法断绝卡洛斯城主的必死诅咒。
那座城如今保留着极好的设施与装备,为了抵抗以太污染和其他不可名状的入侵者,甚至有一位兢兢业业的副官在那里统筹安排,唯独没有属于自己的指挥官。
她看着我,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期待。
“您会去嘛,我尊贵的主人?”
我懒得再纠正她的称呼,顺着她此前的话茬回应:“按着你的说法,我单是坐在那儿就要准备去死了。”
女人眨眨眼,无论是她还是我,明显都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我倒是觉得,不一定呢。”她没有把话说的更清晰,只含糊应着,抬手拢拢自己的头发。
那双手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阿缇耶没有错过我的出神,微笑着,状若恭敬地伸手将我摊放在腿上的手札拿起,放在了旁边的柜子上。
“不是很危险的一本书?”
“用这双手的话,其实问题不大,”阿缇耶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但太长久的触碰也不可以,身体会重现拼凑缝合的疼痛,非常难受。”
“……”我盯着她无辜神色一会,终于还是提起了那个在心里压抑许久的问题,“只有手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