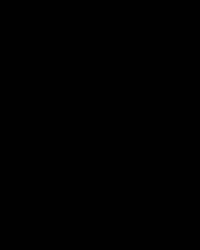云绾宁墨晔小说>望北楼(全2册) > Chapter 03跑马地惊魂(第10页)
Chapter 03跑马地惊魂(第10页)
叶世文心里很酸,伸手替叶绮媚拭泪,明明自己脸颊泪痕仍在。
然后,叶绮媚领着叶世文迈入屠振邦的大门。
这一步,便是一生。
堂前关二爷,神像栩栩如生。美髯长须,衣摆飒飒,脚踩金靴,腰身扎实。冲天的眉,入鬓的眼,红脸一沉,气提丹田,青龙偃月刀砍尽世间宵小之辈。无人敢在此放肆。
叶世文十分听话。净手,磕头,上香,割指,滴血,烧黄纸。契誓立帖,上书蝇头小楷:“屠振邦”在右,“叶世文”在左,生辰八字,父慈子孝,忠义两全。
屠振邦无妻无子,只有五个女儿,分别由不同的女人为他生下。算命佬不敢妄言,只道屠爷八字制杀过度,又逢比劫当旺,得兄弟易得子嗣难。过继一个身强稚子,四柱气势专横,才可安度晚年,有仔送终。
此刻敬天敬地,神谕做证,红盒谨藏。
陈姐在堂外摆素斋。大红烛火在日间似勾魂的眼,摇摇曳曳。祭天公,秉菩萨,得列祖列宗默许,容这位外姓之子过继进来。
成一方气候,旺屠家门楣。
堂内屠振邦与叶绮媚并肩而立,望着这个肃穆端正的仪式。叶世文肤白,那记巴掌印迟迟不消,屠振邦瞥见,低声问:“他不肯?”
“怎会呢?”叶绮媚循屠振邦视线望去,立即解释,“早起被蚊咬了,自己挠的。”
“咬脸上了?”
“小孩子脸嫩。”
“看来是遗传了你。”
一只冷血的手,像蛇行,抚在她腰身后侧。叶绮媚移了半步避开,小声哀求:“屠爷,快礼成了。”
屠振邦不想收手,又探半寸,想摸她挺翘的臀。
“契爷!”叶世文拔高音量,喝了一声。
他站在关二爷面前,烟熏火燎,双颊绯红,讲出这两个不甘愿的字眼。那副脆生嗓音,那道羞愤目光,直直打在屠振邦急色的手上。
无人能料到这个单薄少年,也会长成一百八十五公分的**。
屠振邦位于元村的祖屋,是妈庙路上一幢漆白底铺红方小砖的楼。高三层,占地七百呎,阳台外伸,围罗马柱式栅栏,底雕波纹。
叶世文自屋外迈入,高呼一声:“契爷!”
“文哥仔,先装香。”陈姐递来三支燃起的细香。
叶世文接过,客气道谢:“麻烦陈姐了。”
规规矩矩,腰骨板正,向关二爷、祖宗奉香完毕。
坐在太师椅上的屠振邦,穿白色对襟绸面唐装。盘扣精细,祥云纹路,苏绣针法缀金色细丝描云边,贵气逼人。
金融风暴中屠振邦损失了不少钱,倒不影响他继续奢靡。
他发已花白,气息却沉,瞄了眼叶世文后淡淡开口:“在外面蒲[43]了那么久,舍得回来看我这个老头了?”
叶世文勾起嘴角:“契爷,我以为只有女人才会吃醋。”
“乱讲!”屠振邦撇嘴,“冯敬棠算什么,能跟我比?”
“那肯定及不上你。”
“他是你亲生老爸。”
叶世文绕开焚尽纸钱腾着白烟的化宝盆。双眼轻轻扫过,在所有灰烬里窥得白色一角。纸扎金宝,往往不舍得用这种雪白厚实的纸张,难燃且价贵。
看来他迟了一步。
屠振邦锐眼仍锋利,捕获叶世文的有心探究,不着声息。
“亲生老爸又如何?他又不止我一个儿子。”
叶世文落座酸枝沉木沙发,抓了把花生便开始吃。陈姐受教于屠振邦,格外惜物,平日只拿鸡毛掸子轻轻拂拭,少用湿布,怕伤了木,又蚀了精雕细琢的纹。
屠振邦指着他:“脚放下来!”
“这么小气。”叶世文把腿放下,“最近生意怎样?听元哥讲你斩仓喔。跌到北回归线以下,壁虎断尾,痛不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