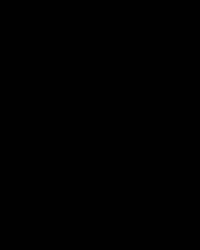云绾宁墨晔小说>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 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自清代以来,“文字起于声音”的观念先后扮演了三种不同角色:在传统小学中,其作用是发明因声求义的原理;在切音字运动中,其作用是为制造切音字提供理论依据;到了汉语拼音化思潮中,它就直接被利用并改造,而成为废汉字的学理基础。如果我们从线性演变的观念出发,这三个阶段无疑呈现出步步推进的趋势,而第二个阶段看起来似乎是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过渡。但从实际后果看,后两个阶段与第一阶段在思路上又呈现出一个根本断裂:本来为训释字义服务的理论变成了颠覆汉字本身的力量。这和社会进化论观点下看到的历史延续性可说是两幅完全相异的图景。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本章所论无疑只是一个很小的主题,但其启示意义不能低估。传统的影子在近代处处可见,怎样理解它们,却见仁见智。在“现代化”思路下,它们往往只是传统的残余,也是需要进一步清扫的对象。近些年,学界试图突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给了这些因素以更加积极和正面的审视。然而,由于仍部分受到线性史观的影响,这一思路常常更多地关注历史的延续性,不免把“现代化”论者视为近代“突破”的那些因素,径直看作传统趋势直接发展的结果。
假如一切都如同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所说,历史海洋的波涛汹涌仅是表面现象,在其深处存在着极为缓慢甚至根本就是“不变的”洋流——它们才是真正决定历史的力量;那么,晚清以来的中国史就正如沟口雄三(1932—2010)所云,仅是土生土长的“前近代”思想的“曲折展开”,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并未破坏这个“结构”,只是“促进了前近代的蜕化”并“因力量过剩造成了一些变形而已”。[134]然则,晚清人常常感叹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岂不成了精神紧张的过度反应?根据本章所揭示的事实,历史其实还有另外的面向:有时,延续性只是一种表层历史现象,向深处追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历史的断裂。
因此,重要的不是近代和传统有多少同类项,而是人们怎样解读它们,给了它们什么意义。这就需要从不同时代文化认知图式的变化来思考问题了。每一种文化,总有一套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整体看法,构成一幅完整图式,决定这种文化对世界的基本观察视角。其具体内容可能随时处在变动中,但只要这个图式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所有这些变化就都可以被消化。历史的断裂实际就是旧文化认知图式为新文化认知图式所替代的过程,而不仅是一个个具体历史现象的改变。[135]晚清以来中国人遇到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底包含了多少内容,恐怕当事人自己也难以说清,但这话却极简洁地传达了他们对此“变局”的整体感受。
回到本章探讨的主题,我们大体可以从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认知图式,一个建立在传统文字学观念上,另一个建立在西式语言学观念上;前者以“象”(包括了形和声,而形较优先)为理论基础,后者以“声”为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字观从汉到清,当然也经过了不少变化,声音地位越来越高,就是一个明显趋势,但这并不足以颠覆旧的六书观念。有一个原因是,传统文字观与天人一体的认知图式密不可分。如前所述,许慎把文字的起源追溯到八卦,两者都是取法天地自然的:八卦是伏羲仰观俯察的产物,文字则源自仓颉从“鸟兽蹄迒之迹”受到的启发。20世纪之前,这个思维图式在中国是基本有效的。[136]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霸权的建立,人们不再通过从自然万物中“比类取象”的方式激发创造灵感,而是从历史的单线进化论中获得知识准则。随着天人一体观的破裂,语言学立场也取代了文字学立场。新图式中当然还有传统因素,但其已从旧图式中抽离出来,经过“再语境化”,被整合到“语言学”中了。它们所服务的是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就是颠覆性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西来认知图式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一个“言语中心主义”而已,它背后还有更深层的观念,如本质与现象的二分。把文字作为“符号之符号”,正如柏拉图把艺术当作“模仿的模仿”一样,深深地扎根在西人对“本质”的向往中。相反,在“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中,这种区分是不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高友工提示的:在中国传统中,文字(“象”)是对自然的描摹,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拟仿,而是圣人对道的“内在”体会的显示,从中可以看到圣人“对生命的了解”。[137]那文字就绝不是简单的“模仿”了。换言之,我们不能单纯地把文字看作声音的记号——似乎声音为首,文字只是对声音的粗劣模拟——而后者正是德里达所揭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内核。自然,本书主题不允许我们对此一重大问题加以详细分疏,我的意图是以对比方式强调,西式观念已成为我们须臾不可离的思维习性,遮蔽了其他视角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思考的结论。[138]如前所述,很多学者并未认真对待其内在理路,就轻易对文字起于八卦的说法置之不理——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这个说法一定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确应该思考,这个传说的历史意义究竟何在;把它当作“原始人”创造的“神话”而轻轻放过,其结果只能使我们错失对“象”这一概念及其更深远的宇宙观意义加以深入理解的机会。[139]
然而,我虽强调确实存在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现代,却不主张回到现代和传统对立的二元思维。即使延续性只是表层现象,也不意味着它不再重要了。处在历史变局中的人们虽对整体性的文化断裂有着清醒认识,但当他们运用各种更为具体的思想资源时,常轻松越过两个根本不同的认知图式,在中国的和西洋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因素间自由滑动。当汉语拼音化论者援引传统声义说作为废汉字的依据时,他们未必是要刻意“利用”传统,而只是将自己早已掌握的知识与新观念结合起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思想的“化学反应”。如同我们要尊重当事人在整体上的变动感一样,对于他们的“不自觉”,我们也应充分尊重。正是在这种“不自觉”的掩护下,新的文化认知图式才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去颠覆了旧的认知图式。
[1]历来论汉语拼音化运动的著作,很少注意文字观在其中的作用。对此给予了较多关注的是申小龙的《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4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但他讨论的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的争论,其意图也主要在“论”而不是“史”。
[2]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15~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言语中心主义”亦译为“声音中心主义”。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Assmann)对亚里士多德语言观的解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286~2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不过,西人对此问题的认知也不是只有一种。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有人曾认为,文字早于口语。直到20世纪,这个观点仍有接受者。(详见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62~63页。)福柯(MichelFoucault)也指出,在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描述中,“视觉”占据了一个优先地位。近年来,一些社会学家亦开始反思这种“视觉中心主义”的影响。[安东尼·伍迪维斯(AnthonyWoodiwiss):《社会理论中的视觉》,魏典译,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瓦尔特·米尼奥罗指出:早期近代西方文化中,亦曾出现以“书写”来压制“言说”的现象。(瓦尔特·米尼奥罗:《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141页。)因此,我们在援用德里达理论的同时,也必须充分注意到“西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不过,本书是在高度概括的层次上涉及此一问题,目的在于通过比较研究,展示中国文字观的特性。实际上,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西人的“视觉中心主义”与“声音中心主义”之间恐怕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关系。唯此已远离本书主题,无法在此处展开。
[4]汪荣宝:《法言义疏》,2~3页(卷页),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91。
[5]在中国历史上,文字一开始就具有相对于语言的独立性,而这应该是和其诞生之初的环境、功能分不开的。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Vandermeersch)通过对甲骨文的考察指出:“中国表意文字体系不是作为话语的书写被创造的,而是作为一种配置的象征体系被创造的,以直接表述占卜的参数与结果。”在“与口语完全分离”的意义上,汉字和文言是一致的,不过这不意味着表意文字系统和口语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事实上,他还列表说明汉字和表音文字之间的差别。在表音文字中,从所指到能指的关系链是:
文字(能指)→发音(所指)→词意(所指)
而在表意的汉字中,这个关系是“并联串接”式的:
文字(能指):
→词意(所指之意)
→语音(所指之意的读音)
这一叙述与我这里的看法颇为接近。(详见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金丝燕译,4~5、26~27、52、104~1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不过我认为,汪德迈讲的这两种关系在汉字中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而第二种关系更能体现出汉字的特殊性。
[6]当然,“象”一定有“形”,而并不一定要有“形”才可“象”。班固所传“六书”义,就把许慎说的“指事”称为“象事”,“会意”称为“象意”,“形声”称为“象声”。
[7]孔颖达:《周易正义》,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1册,157~158、166、168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
[8]陈梦家:《中国文字学》,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9]吕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见《文字学四种》,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陈梦家:《中国文字学》,17页。唐兰:《中国文字学》,5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9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10]高友工认为,从许慎开始,文字“才真正地”被“推到一个尊贵的地位”,形成一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现象和“文字至上的心理”,语言则“相对地退居其后”。参见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见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138~1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1]郑樵:《通志二十略》,340、350~3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254页。
[13]汪康年:《汪穰卿笔记》,19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5]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91~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6]傅懋勣(1911—1988)认为,“右文说”和“音近义通说”是中国训诂最重要的两个原则,而“音近义通说”是“右文说”扩充的结果。(傅懋勣:《中国训诂的科学化》,见《傅懋勣先生民族语文论集》,25~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本书则将二者合而论之,不再做细致区分。
[17]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29页。
[18]丁邦新:《以音求义,不限形体——论清代语文学的最大成就》,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胡奇光:《中国小学史》,2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0]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不严格遵循德里达的原意。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第三十四”,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22]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25页。
[23]凡是讨论中国语言学史、训诂史或语源学史的著作,在涉及此问题时,基本都遵循了沈兼士勾勒的线索。除了前边提到的王力、丁邦新、胡奇光等人的著述外,亦可参见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此外,於梅舫在讨论陈澧的小学观念时,也对清儒“以声韵贯穿训诂”的取向做了清晰的勾勒,参见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137~14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