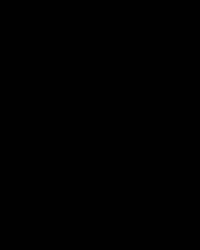云绾宁墨晔小说>万人迷女主的前夫们 > 分食(第14页)
分食(第14页)
但他的心的确是有些乱了。
苏予辞知道,这种不该有的情愫是心动,但也只是心动,还没到喜欢的程度。
灵力自指尖而出,凝成一支箭矢,擦过姜稚鱼的耳际,在姜稚鱼还没反应过来时贴着她的脸颊飞逝而过,钉在裙摆绣着的牡丹上。
一缕断发徐徐坠落,苏予辞眼前又浮现出北渊那片艳红的梅花瓣,从遥远的高处来,摇摇晃晃,单薄地落在他的掌心。
苏予辞将那缕发丝攥入手中,用平铺直叙的语气,客观地陈述道:“懦弱又愚蠢,是个废物。”
姜稚鱼,你最好祈祷,我不会爱上你。
容絮耸了耸肩,慢腾腾地回道:“她的确不怎么聪明。”
在那一箭射出时,容絮并没有拦,拦与不拦都已经一样了。
“但既然苏道友都知道她是废物了,还那么苛责废物做什么?”嘴角噙着笑,容絮悠悠开口,“况且,废物不好吗,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毫无心里压力地贬低着自己口中所爱之人,一点顾忌也没有,就像很久以前那样,人是扭曲的,爱也是扭曲的。
苏予辞沉默不语,抬眼,和容絮对视了一眼。
这一眼,实在是很微妙。
男人,总是在某些方面有着某种心照不宣,更何况是他们这样身处高位的人。
他们很少会去思考喜欢一个人该怎么办,喜欢与否都是一样的,绝对的权利压制下,从来都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正如情爱不是必需品,需要时可以拿过来用,不需要时便可以抛至一边,或许偶尔,也可以因利益纠纷拿来共享。
容絮说爱,这爱,也不过如此。
苏予辞轻轻地笑了:“你说得对,她聪明不聪明的确是不重要的。”因为这与我对她是否存有欲望毫无冲突。
他微微侧首,看向姜稚鱼,突然开口:“人快要被我们弄傻了。”
“没办法,胆子太小了,不经吓,”容絮皱着眉,似乎很烦恼,“只能把她的记忆改一下,麻烦。”
“好不容易才相处的一段和谐时光,就这么被抹去了,真可惜。”
说得好像没有这事她就可以不用修改记忆一样,他们干的那些事就注定她要被迫选择遗忘,苏予辞不置可否:“你来还是我来?”
容絮拿出一支烟管,点上,懒懒散散地回道:“都行。”
他怕自己用力过度,不小心伤了她,他现在还有点控制不住。
苏予辞朝姜稚鱼走过去,一步步逼近:“那便我来。”
姜稚鱼抱着自己,脊背紧贴着结界光屏,退无可退,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能这样神色自若地交谈着,尤其是在做了那些事情之后。
这一刻,姜稚鱼绝望到了极点,她无法想象,站在她面前的,究竟都是什么样的人啊。
苏予辞穿过结界半跪在姜稚鱼面前,手臂从她腰侧穿过,扣住小腹将她扯向自己,环抱入怀中。
掌心贴在姜稚鱼额间,苏予辞声如春雨,字字不顿:“姜姑娘,我不是很喜欢你之前那样的眼神,再有下次,我会把你的眼珠子给挖出来。”
鼻子发酸,眼睛酸胀,姜稚鱼还未应答,一滴泪水已经坠落下来,她知道,这是一种明知身处逆境却无法逆转而产生的悲哀:“嗯。。。。。。”
灵力钻了进去,片刻之后,苏予辞放下手,揉了揉眉心:“情绪波动太大,直接来会对她的身体造成太大伤害,她承受不了。”
烟管燃尽,容絮也跟着进来:“那就先给她喂点药。”
听着他们用分享物件的口吻摆弄商议着自己,姜稚鱼忍不住低下头,身体也不听使唤地战栗。
容絮蹲在她面前,防止她挣扎踢踏,将她蜷缩的腿拉到他的腰两侧,固定住后,手里凭空多出一碗黑乎乎的汤药,散发着奇异的气味。
汤勺递到姜稚鱼嘴边:“乖,张嘴。”
姜稚鱼看着那碗药没由来地感到恐惧,往后缩,背后是苏予辞,往前探,身前是容絮,她被夹在中间,怎么躲都躲不开。
下巴被掐住了,姜稚鱼以一种乖顺的姿势倚在苏予辞的怀里,眨着大眼睛看着容絮,眼泪直淌:“我会听话的,能不能不要欺负我。。。。。。”
筋骨分明的冷白手掌掐住姜稚鱼的脸颊,红艳的小嘴被脸颊的肉挤得微微嘟着,苏予辞低头撇了她一眼,看着那张惨白的脸,简短地解释道:“不会对你的身体有损害。”
姜稚鱼不理解,还要再听话一点吗?可她已经很听话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