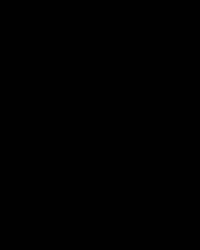云绾宁墨晔小说>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 二不良文艺的负能量(第1页)
二不良文艺的负能量(第1页)
二、不良文艺的负能量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当时的讽刺作品、粗俗文学等的负面影响。“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势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38]宗教改革时期的粗俗文学,在鉴赏力不高的人那里产生不良共鸣并引起一些人在美学上的反感,其艺术影响几乎全部是负面的,或者谈不上艺术。一些偷梁换柱、混淆视听的观点,不仅表现出“有曲解本人的天才”,“还有被人曲解的天才”。马克思对雨果的观点及话语多有指责,认为他的高谈阔论和无聊言辞,是对巴黎公社的无端攻击,对卢格的可憎语言,陶森瑙、梅茵之流的诽谤言论,马克思也予以揭露和剖析。
旧思想、旧文献的影响是保守势力经常关注并竭力维护的,但这种力量的影响是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时指出:“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39]1848年革命中,《法兰西报》和反动派的报纸都起过鼓动作用,因为欧洲的一个讲坛道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秘密,“《通报》在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脸红了,这些‘荒诞呓语’原先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伪经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40]。在革命中,代表各种思想愿望的报刊或宣传机构,都希望一显身手。当巴黎戒严解除和报刊恢复时,“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期间,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期间,立宪君主派小资产者的老的代言者《世纪报》共和主义化了;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的喉舌《新闻报》民主主义化了,而共和派资产者的老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社会主义化了”[41],那时在经济上无所作为的工人协会,在政治上却对无产阶级起着纽带作用,这与一些媒体的宣传作用分不开。为了强化自己的舆论力量,秩序党希望以自己的喇叭声驱走自己的恐惧,有刊物高喊“剑是神圣的”,有刊物要求对“红党发起进攻”,有刊物声明“要消灭社会主义”,最后这些刊物无一例外地帮助秩序党重弹“加强镇压”旧调。在《德国革命与反革命》中,针对德国文坛鼓吹不成熟的立宪主义和不成熟的共和主义的倾向,恩格斯这样写道:“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低等文人的习惯。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的流露。”[42]为了迎合当局的新闻出版政策,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散布着杂乱的思想,把曲解了的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入其中,“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既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样也把检察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坛的其他任何一个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43]。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杜林标榜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作品”斥为“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和“白水似的作品”,是“老生常谈”和“施给乞丐的稀汤”,“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44]。这种教育技术脱离了以后的实际运用,失去了生活的本义。马克思刚去世,《最新集萃》杂志就发表文章,包括错误百出的传记、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方面的批评,阿基尔·洛里亚极力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消极作用在当时影响很大。“在那里,他以一种自信态度伪造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态度让人推测出他抱有一个巨大的目的。”[45]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思想的公然诋毁和反叛。
对于民族文化不良内容的负面影响,列宁认为,它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滋生产物,不仅不能保护异族人,反而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大民族主义“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过错的”,比如:对异族人的蔑视,“把波兰人都叫做‘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46]。这些恶俗陋俗是不良传统文化的遗存,对民族团结而言是一个消极因素。也有一部分人沉溺于旧的传统文化而无视不良影响,“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47]。即使是接受了苏维埃思想的工人中,即使是被苏维埃社会主义思想感染的工人群众,也没有完全肃清头脑中的落后意识,也经常受到传统遗留的不良思想的影响。
在列宁看来,我们的机关仍然具有旧社会的痕迹,而且这种旧的机关时刻试图显示出保守的力量,旧官吏的不良意识,旧社会的思维惯性,旧制度的不良内容,都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并影响着苏维埃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我们要在这里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要证明我们不是只会死背昨天学到的东西和重复过去的老一套”[48]。由于旧东西客观存在,它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旧东西中并不完全都是不可接受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内容,“旧东西我们不应该拒绝”[49],旧社会的有价值的发展方式、管理方式,都是需要借鉴和利用的。在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主义是一种不良文化遗存,起着消极作用,不能隐瞒它,而要揭露它,这是无产阶级对待不良文化遗产的基本策略。
斯大林在《论〈红色青年〉杂志的任务》中指出:要看到一些刊物的不良作用。列宁说:“卢·乔·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分是臆想出来的;对十分明确的历史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注意到最本质的东西(即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等)。”[50]一些文学作品的创作思路、内容表现都显示极左思维,把革命形象打扮成完人,把不良现象完全归结为资产阶级立场,在反右的同时又走向左的方面,“作者在摒弃‘工团主义的抵制’、摒弃‘消极的’抵制的同时,臆想出一种特殊的‘积极的’(哦,多么‘左’呀!……)抵制,这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断的错误极其严重”[51]。这些“左”的做法,使西方国家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有了攻击的把柄和口实,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来诋毁和污蔑社会主义国家。“在最富有的国家内,花数千万金钱推销数千万份来散布资产阶级谎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在重复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论据和责难,说美国、英国和瑞士是以民权制度为基础的先进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却是强盗国家,没有自由,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思想,甚至解散了立宪会议。”[52]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吹得很,实际上是平常的小资产阶级崇拜的“英雄”,在吹嘘中被赞扬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猎人”“世界上最伟大的爬山家”“世界上最伟大殖民家”,这种吹牛最终使他的朋友丧失体面、羞愧无地。
一些杂志,如《自由》杂志,因为矫揉造作,不使用“民间的”比喻和“民间的”词汇等群众易于理解和需要的方式,“作者就是用这种畸形的语言,翻来复去地谈论那被有意庸俗化了的、陈腐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不引用新的材料、新的例证,也不进行新的加工”[53]。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是极其糟糕的,它不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刊物。在列宁看来,通俗作家不是庸俗作家,通俗作家要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和研究,经常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恰当的例子或通俗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引导读者独立思考。“在庸俗作家的眼里,读者是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的,他不是引导读者去了解严肃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下去就行了。”[54]